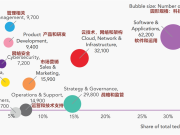(编者的话:台湾出生、美国受教育,林夏如曾是高盛集团亚洲区最年轻的合伙人。过去的投行工作,让她以香港为家,操盘亚洲投资决策。在香港移交主权20周年前夕,她写下身为一个台湾移民,对香港的观察和期许。)
1992年我只身到香港,一转眼已经25年。香港回归20周年纪念日对我来说是特別有意义的,那时候有些人虽然因为回归而出走移民,但我因为加入投资行业而决定把香港当做自己的家。这是个改变我人生的决定:我在香港进入互联网风险投资行业、也成为三个香港小孩的妈、后来进香港大学念政治经济学并开始做老师。我清楚地记得,在回归前夕,尽管香港政府更迭和对“一国两制”实验充满着不确定性,但大家的心情非常乐观,因为“港人治港”终于要实现了,而当时没有多少人担忧2047年以后的事情,只期盼“高度自治”得以成功实践。
二十年时光飞逝,今年7月1日林郑月娥就任香港行政长官(特首),她是香港历史上首位担任这一最高长官的女性,理应赢得掌声。然而,在这样历史性的时刻,日益极端化的香港社会并未有多少欢呼与喝彩。香港的行政长官并不具备广泛的民意基础,林郑月娥自身的受欢迎程度亦有限。事实上,今天不少香港年轻人们认为香港价值和自主性早已经被侵蚀、“两制”早在2047年到来之前就已经不复存在。
在香港年轻人眼中,今年3月参与行政长官选举的3位候选人都不意味着改变,也缺乏合法性。林郑月娥获得了1200名选委的777票,比五年前当选的现任行政长官梁振英的689票要多,但她依旧未能赢得泛民主派的任何支持。在现行香港立法会的运作框架下,政府若不能取得跨政治阵营的支持,政策将难于推进。此外,林郑月娥在社会福利、环境保育和政治改革方面都持强硬保守态度,三年前“雨伞运动”中亦拒绝回应学生的诉求,十年前也是她强硬面对“保卫皇后码头”运动示威者。
当前,香港政府最亟需应对的问题其实是在经济领域,因为正是经济问题让社会加速极端化。
日益分化的社会
香港经济增长正在放缓,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资产持续膨胀。上世纪70至80年代香港人均 GDP 增速维持在6%以上,而过去5年里这一指标仅为3%。劳动阶层和年轻人的就业机会有限,因为香港产业结构单一,就业市场无法多元化。 1981年,香港人口年龄中位数是26岁,回归前一年,这一数字已经超过34岁了,今天更上升至44岁,在“亚洲四小龙”中属最高。尽管在过去20年中有大量新移民到来,过去10年里人口增长速度有过短暂回升,但香港的人口成长速度依旧缓慢(下图图一)。

同期,香港的房价已经攀升至匪夷所思的程度。 国际房价负担能力报告(Demographia International Housing Affordability Survey)的数据显示,2016年第三季度香港平均房价是本地家庭年平均收入的18.1倍,即一家人不吃不喝18年方能“上楼”(买房),年轻人无法置业。上述问题所衍生出的是一个日渐分化、充满隔阂的社会:泛民与建制派,新移民与老香港人,精英与草根之间互相对立。类似的情形同样在美国、英国、台湾、韩国等地产生。我将它称之为“高收入陷阱”——这个问题在高收入经济体的四小龙最为显著,他们都在发展至一定程度之后经济成长开始放缓(下图图二),各种社会问题接踵而来。

落入“高收入陷阱”的社会普遍面临的问题包括生育率下降、房价高涨、年轻人发展机会受限、社会贫富悬殊日益严重。根据香港政府发表的住户收入分布统计报告,2016年香港的基尼系数为0.539,已达到45年以来的历史新高,其不平等程度位于世界发达经济体之首(图三)。这样的地方对任何领导人都是巨大的挑战,更何况在一个缺乏民主代表性的机制下,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难以发洩,彼此之间的矛盾也更难于化解。

身分认同的代际分歧
伴随这些经济问题而来的是认同的改变。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数据显示,近年来香港年轻世代(尤其是没有受过英国殖民教育的一代)对“香港人”身份认同感不断加强,仅有3% 的年轻人认为自己完全是中国人。持有强烈“香港人”认同的年轻人数量是老一辈的两倍(下图图四)。三年前的香港几乎没有人主张“港独”,而现在尽管大家都知道“港独”没有出路,这一议题还是引发年轻人的关注,“本土派”随之产生。同期大陆在其他城市推行高压的政治管治,言论自由被扼杀,也引发香港人的反感。因为缺乏民主代议制度,以年轻人为主的社群无法将自己的认同和诉求有效表达,只好诉诸极端立场,以彰显自己“与大陆有別”。老一辈香港人觉得香港最珍贵的是法治,年轻人觉得香港的核心价值是对民主的追求。这是一种著眼于身份认同的抗议,也是代际之间的分歧。

认同的另一个指标是对宪政体制的信任。香港大学的民调也追踪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任度与不信任度,二者之差即是“信心净值”。回归时,有信心的人比没有信心的人多三成(下图图五),2008年前后,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高涨,信心净值超过五成;而从2014年“雨伞运动”以来,香港人的信心跌至回归以来最低谷,这一指标出现负值,直到现在都低过 2003年沙士(SARS)恐慌时期。不信任“一国两制”的香港人越来越多,不少香港人认为“一国两制”的根基正在被逐渐侵蚀,不用等到2047年便会告终。

参照台湾在与大陆进行经济集成过程中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身份认同和核心价值的争议会让激进的政治立场得到惊人支持,利益分配不均等经济问题更会火上加油。所以陈水扁时期,台湾对大陆经济政策就在极端选项之间摇摆。但是过去这十年,台湾认同一旦巩固,大部分选民都觉得自己是台湾人,台湾的大陆政策反而越来越理性。国民党在2014年草率通过的服贸协议最终被大众阻止,民进党去年再次执政后对大陆态度也远比过往审慎。因为人民“话事”,两党政策摇摆的空间有限,会越来越往中间选民靠拢。这种政经分离的趋势在台湾年轻人中最为明显。在两岸经济、社会交流加深环境中成长的台湾年轻人,对大陆就业机会并不排斥,但同时他们正是“天然独”的一代。我们常听说大陆经济成长会导致年轻人自然接受中国人的认同,其实,当具有不同价值观的社会发生碰撞时,经济问题更会导致大家对认同的分歧突显,而认同是不会因为商业往来而自然结合的。
在过去,香港人较为务实,善于将身份认同和政策偏好分开;而台湾则一度因身份认同的极端化导致相关经济政策不能在理性的环境下讨论。如今,台湾社会三十年来在身份认同和对大陆政策的激辩,在短短三到五年内搬到香港上演,两地的社会氛围正好调转:台湾社会在民主机制下的反复讨论中不仅巩固了台湾认同,也形成了基于“台湾优先”而对大陆经济政策、尤其是两岸制度化协商的共识和支持;香港则在最近陷入日益频繁的认同、所以对任何和大陆有关的政策都备受争议。即便是那些经过周密思考、对香港经济有益的政策,也同样会招致部分香港人的不满。
不必为香港未来过于悲观
虽然香港是个移民社会,大部分人都是从大陆陆续过来,但以前来的移民都要接受香港价值的洗礼,现在则是新移民——无论菁英或基层,似乎都在改变香港的价值与文化。过去,治理香港的多是相当有能力及经验的人才。现在,香港人觉得香港正被来自内地的新移民占领,不是炒楼的富豪、就是排队等公屋的家庭,让本地人觉得有限的资源被抢占。而政府要员比较看重的是如何揣摩北京的意思来管制特区,没有把香港的老百姓的苦衷转述给北京。这对香港人来说实在难以接受,也极具讽刺意味:“一国两制”本是邓小平为实现统一台湾量身定做的,但如今香港的模式对于台湾而言毫无吸引力。
身份认同问题导致政策偏好极端化的例子在香港已经不少,但争议将会越来越多。例如林郑月娥提出的“西九龙故宫文化博物馆”计划,这一计划或许有利于香港吸引更多游客、丰富香港社会文化生活,但很多香港人却视为暗箱操作,有悖香港精神,这正与台湾反服贸的“太阳花学运”相似。香港社会对“广深港高铁”采取“一地两检”安排的争议又是另一个代表案例:这一项目将内地和香港更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允许内地执法人员前来香港执法,这会让争议更加激烈。即便这条铁路有利于香港经济发展,香港人却只看到跨境执法如何的触及“两制”的底线。在未来,林郑月娥将会持续面临类似的治理挑战,尤其是在处理与立法会关系和推动政策出台方面,她的处境与当年台湾的陈水扁其实颇为相似。日前林郑月娥接受大陆官媒采访时甚至表示,要从幼儿园开始培养小朋友的中国人认同,这只会引发香港社会更强烈反弹。身份认同是勉强不来也压制不住的,香港年轻人“反国教、撑普选”,就是在用看似极端的手段来强调身份认同和价值观。
如今的香港与三十年前的台湾在社会极端化方面如出一辙,但有所不同的是,中国大陆中央对香港的制度有著高度干预的能力,例如行政长官选举。十九大之前,中央一定会继续坚持对港台采取强硬立场。对中央政府而言,还有太多比“了解港台社会变化的细节、制定好的政策”更迫切的事情。在他们眼中,让香港服从管治比为香港社会带来切实变革更为迫切。但是,经历过三个北京钦点、不是坐牢就是极度不受欢迎的特首之后,中央继续为强硬派候选人背书只会让问题的雪球越滚越大。如同梁振英一样,林郑月娥深知北京是她权利的来源,所以不太可能去修补香港不同社群、不同代际之间的分歧,而中央很可能继续现有的香港政策,让建制派阵营享受经济利益,对其他社群呼吁推动政治改革、捍卫香港自主性的声音置若罔闻。
当然,将地方政府施政过程中的问题一律归咎到中央是一种误导。香港要跳出“高收入陷阱”,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也要面对认同的分歧。这一切都要从凝聚社会共识开始,而这正是香港政府未能做到的。但中央对港澳台事务缺乏关注的确是导致问题恶化的重要原因。虽然大陆港台事务专家充分了解到这几年年轻人的趋势,但中央政府在处理对港台问题时始终处于守势,一旦发觉情况不妙就采取强硬立场,结果适得其反。遗憾的是,如果中央尚未意识到政策调整的必要性与迫切性,香港也将面临日益极端化的社会。人非草木,要强行将一个长期与大陆分隔、贫富悬殊,保有自己独特文化历史记忆的社会加以融合,本非易事,更何况大陆自身经济挑战巨大。
不过,正如我们不应在1997年时过于乐观、笃信“马照跑、舞照跳”,我们如今也不必对未来过于悲观,毕竟“一国两制”是一场独一无二的政治实验。今天一些中央政府官员、内地不少年轻人以及香港人都认为“一国两制”是失败的,北京怪香港“不够听话,不感激”,而香港人则担忧中央已经打破对“高度自治”的承诺,香港自主性不受保护,双方的认知隔阂正在不断增加。但是,香港社会有很强的韧性,善于灵活应变。我也相信,香港年轻人有著强烈的参与热情,希望香港会发展得更好,所以才走向街头。我一直鼓励我的学生们热心关爱自己的社群,尽管每个人对“社群”的理解或许不一,如果香港年轻一代有心关注公共政策、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来回馈社会,那么或许他们会带领香港,以公平正义为基础,定制好的公共政策,走出“高收入陷阱”,创造一种具有包容性、富于同理心的香港。包括我在内的无数香港人正是因此将这里视为自己的家,为香港感到骄傲,我们自然也有责任让她在未来走得更好。
(作者目前同时任教香港中文大学及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过去曾任高盛集团合伙人,也是阿里巴巴、中芯国际董事会的创始成员。最新著作《台湾的中国两难》(Taiwan’s China Dilemma,中文书名暂译),中文版预计九月份在台湾出版。个人网站:www.shirleylin.net。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