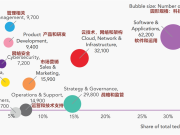中国目前是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经济体。如何洞察和理解中国的经济走势成为一个非常迫切的课题。在通商中国主办的慧眼中国环球论坛上,时代财智专访了中国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兼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必亮教授和中国富春控股集团董事长张国标先生,他们的观点透露出的信息是,中国经济基本面是非常稳定的,或存在一些结构性的问题需要调整。

“我觉得此次通商中国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平台,让新加坡的朋友来了解中国的过去,现状和未来趋势。”张国标先生身材高大,声音洪亮,他在采访一开始就谈到新加坡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中国经过30多年的发展,国民经济基础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化,在发展过程中,新加坡也作出了巨大贡献,连续很多年新加坡都是在中国外资投资最大的国家,新加坡在中国的城市管理和建设方面,人才的培养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新加坡和中国有着特殊的关系,苏州工业园就是一个很好的合作模板,在城市发展,工业发展,产业园发展方面都具有指导意义。”
三驾马车决定中国经济基本面
张国标认为要观察中国今天的经济走向,必须看投资,出口和消费这三驾马车。
“中国的投资可以分为不同的阶段来看。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之后,当时百废待兴,进行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随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几年的投资,不仅规模比那个时候更大,在投资的质量和能级上,完全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从区域看,除了沿海东部投资发展比较快,现在中西部联通的投资,区域经济平衡的投资也大大加强。”

张国标介绍,中国城市的发展从之前的粗放型模式到能级提升,功能完善型的投资也加大。在投资内容上,原来是只求生产发展,修工厂,修电厂,修公路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到现在环境友好型投资,更多地投资医疗和教育,投资科研,投资生态,环境科技,而且投资增量很厉害,这样的投资,对相关产业的发展拉动是必然的,“这奠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
中国的出口领域也呈现出许多新的变化。
中国目前正在进行产业升级,衣帽鞋袜皮箱这样的低附加值行业都转移到东南亚、印度和孟加拉了,“现在华为或者中信的一台设备,出口的价值和利润可能相当于过去一整列火车的产品的规模。中国的出口产品实现了劳动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的转型,现在出口服务,出口资本,‘一带一路’,意味着资本、技术、系统和人才以及文化的出口。”
谈到消费,张国标认为,中国过去是温饱型消费,再过度到第二个阶段以吃穿住行为主的大众消费,再到现在的医疗消费,旅游消费,健康快乐消费,文化消费,等等更高层级的消费。
“这三块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非常稳定的,”张国标说。
“同时中国现在正经历这城市化和人口结构变化,2015年到2030年之间,城镇化人口要达到9亿人,在城市生活的人要相当于3个美国的人口,中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是西方国家的人数总和。”
知识型的劳动密集型经济
就此张国标还提出了一个“知识型的劳动密集型经济”(Labor Intensive Industry Based on Know-Hows)的概念,他指出,中国航天科技和通讯科技能够在二、三十年间迅速赶上欧美,正是因为中国的教育体制培养了大量刻苦钻研技术的工程师,他们的工作强度和规模,在西方国家是难以想象的,“所以中国未来的科技创新能力是全球领先的。”
另外,中国高净值人群的基数非常大,到了2030年,中产阶级人数达到3亿人,这些人都是80后90后,他们具有很强的财富创造能力,超前的消费理念,这都决定了消费水平能级提升,实现几何式增长。“世界上现在同时流行‘中国威胁论’和‘中国机会论’。说实话,中国哪有时间去威胁别人,我们满大街的人都在万众创业,大众创新,内部不搞阶级斗争,外部只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认为‘中国机会论’其实是最符合现实的。”张国标表示。
对于目前中国盛嚣尘上技术产业提升造成失业的说法,张国标表示不用担心。“中国的建筑工业现代化的确不需要太多劳动了,因为建筑现在都是预制装配。但是中国在其他领域,比如服务业是非常需要人力资源的,中国最缺的是护士和保姆,现在的医养专业的人力资源连未来需求人数的十分之一都不到。过去是独生子女政策,二胎放开后要30年后才有劳动力。所以中国服务型的行业可以吸收大量劳动力。”
谈到富春在中国的经济大潮中的的成功经验,张国标认为自己作为浙商并不比其他地区的人更聪明,靠的是勤奋,以及创业在上海,“上海是中国的经济重心,经济风向标,我们比其他地区对于商机知道了解得更早,而且我们浙商这个群体,抱团,相互学习,马云,郭广昌,丁磊,这些人物或多或少影响到周边的群体。”
他还透露,富春到新加坡来上市,实现国际化,是因为新加坡的市场开放程度高,法规制度透明,国际化程度深。富春希望在新加坡这里跟东南亚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联动,“新加坡是富春基于国际化需求综合考虑下选择的。”
不能再通过结构扭曲来保增长
中国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兼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必亮教授上世纪90年代曾在新加坡从事投行工作,有着非常的丰富的经济领域的实践经验,对中国和世界经济都有着十分深刻独到的见解。

他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总体不错,就算不进行结构性调整,今年受到的影响不大,因为目前全球的经济形势普遍好转,中国出口非常强劲。但今后几年就很难说了。
中国的改革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政府的行政力量来强行进行扭曲,比如投资不行了,政府就增加投资。“中国政府权力很大,没有钱政府就印钞票,但是这会造成新的扭曲,带来负面影响,因为货币太多,所有的资产价格都很高。现在房价这么高,就是因为货币太多,年轻人无法生活,这个地方就没有活力了。博士学位干得再好在这里也无法买房,所以年轻人才都流失了。”
在国际贸易方面,政府不断刺激出口,导致中国和各国关系都紧张,“人家贸易逆差,中国贸易顺差,从长期的发展来说是不利的,因为别国都不来做生意了,所以通过政策措施暂时保了增长,但长期而言是不利的。”胡必亮说。
谈到中国国内的经济结构,胡必亮指出,现在中国很多行业仍是政府在垄断,应该打破这种垄断,让私企和外企都进入这些领域,才能让经济获得活力。“民营投资和国有投资的回报差距很大,甚至高达差一倍。被国有企业垄断的行业效率低下,如果让一些份额出来,让私营和外资进来,生产效率就提高了。现在搞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就是让私营和国企联合起来做一些项目,提高生产效益。”
胡必亮还认为,国企改革的重点在金融改革,中国金融市场不完善,大量的钱放在银行,流动性很差。“这种间接贷款的模式,让所有人的钱都是通过银行来贷出,银行来帮着运行,没有积极性,如何从间接融资到直接融资,通过完善资本市场,这个空间非常大,通过改革来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潜力很大,比政府扭曲市场来得实在,后遗症更少。”
地方债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另一颗“地雷”。现在地方政府债务主要问题是,一些地区过度依赖负债投资的冲动非常强烈,地方债增长的速度过快,每年高达20%以上,大大超过GDP和财政增长速度,有些区县和西部地区债务余额增长甚至超过1倍。地方政府债务率高,一部分省市超过或逼近100%警戒线,偿债压力大。地方举债主体下移,基层市、县、乡负债比例普遍偏高。地方政府债务与土地财政、影子银行等其它风险点交织在一起,容易互相传导,相互感染。违法举债、变相举债仍有发生,“隐性债务”野蛮生长。
对此,胡必亮的看法是,地方债是中国发展模式自相矛盾的产物。
“中国前几年经济发展得这么快,和地方政府的努力分不开,一个地方的首长,市长就相当于一个城市的总经理,他们把城市当公司在经营,所以效率很高,但公司经营必须融资,过去是靠土地财政卖地来筹钱,现在随着制度和法律的完善,这样做受到了很大的制约,于是就建立新的融资渠道(举债)来做项目。”
中国经济最根本问题是体制改革
胡必亮认为应该警惕地方政府的短期经济行为。“政府搞经营本来就是是对私营不部门的不公平,政府应该是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在中国,各种要素都被政府控制,从事经济活动必须和政府合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政府不能和私有部门竞争赚钱,政府应该实现转型,把职能定义清楚。反腐败必须釜底抽薪,只要政府还在搞经营,很容易赚钱,设立国家财政体制外的小金库,所以就容易腐败。西方国家政府很难腐败有个原因就是是因为自己不搞经营,很难碰到钱。”
“习近平主席领导的反腐运动有很强威慑效果,腐败行为得到了有效遏制,”胡必亮表示,“地方政府的越权越位行为要从制度上纠正,只要滋生的土壤存在,腐败还是会反弹,如何改进中国政府的治理方式是根本性的手段,要做到从制度上逐渐不能腐。”
谈到中国的房市,胡必亮表示房价里面存在很多泡沫,泡沫现在还没破,是政府在扭曲。“这么大的泡沫,没有实际的需求,总有一天会破灭,会有金融危机发生,房地产商大量举债,如果无法还贷,就会造成银行坏账,这几年银行的坏账是增加的,如果继续通过政府的政策增加信贷,坏账就会继续增加,更重要的是中国很多产品都是生产过剩,增加投资后生产的产品是社会不需要的,变成库存,对GDP有贡献,但没有实际价值。”
胡必亮认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不希望房价下来。因为开发商的资金绝大部分来自银行,房价下来导致房地产行业和国有银行都出事,政府尽量通过政策把房价稳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但是通过政府行为强行托市,和市场的真实需求不吻合,泡沫最终还是要破灭。“中国北上广深是绝对稀缺的资源,和新加坡、纽约这样的国际大都会一样,房价永远都很高,但中国的二三四线城市就不同了,经济上行房价自然高,经济下滑就撑不住了。通过超发货币来救市会造成恶性循环,在中国,房子和很多人一辈子,甚至是几辈子都没有关系了。”
“不能再通过结构扭曲的方式来保增长,要通过改革的方式来保持经济增长,改革还有很大空间,比如完善农村和城市的产权,让农民更有积极性,现在农业生产效率很低,很多年轻人都离开农村了,农村的土地基本没人种了。通过土地流转,可以让农民获得更多的收益。”
胡必亮认为,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处在快速转型的过程中,过去传统经济产业发展支持的高增长模式不存在了,需要新的模式维持高增长。“过去是制造业,但是制造的东西都过剩了,对GDP的贡献过去超过50%,现在低于40%,所以要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创新,走出去,搞‘一带一路’。”
“中国经济最根本的问题是还没有过度到以市场来配置资源的主导作用,大量的资源还是行政配置,”胡必亮在采访的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