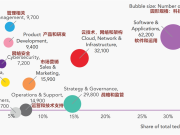今天《联合早报》刊登的两封信,主题围绕崛起的中国。新加坡年轻人如何看待中国,与他们是否真正接触过中国有关吗?《联合早报》记者黄伟曼认为,当她走在中国城市的街道上时,自在的感觉并不源于任何抽象的文化认同感,她相信新加坡人能理性地去认识中国的变化;《海峡时报》记者袁昕则说,即便是在讲英语的新加坡华人当中,把中国当成落后国家,已经是过时的想法,大家都认识到,中国越来越“酷”了。
致袁昕:
22岁那年,我第一次独自旅行,记忆中上海的繁华街道,成了我对当代中国的第一印象。
那是2010年,上海也举办世界博览会。在夏日的高温下,受困于长长的人龙,等待入馆参观时,我只能自得其乐,以观察周围的陌生人来打发时间。不过,原来若见有人插队应心生厌烦,看到队伍中大伙儿为降体温,用舌头“集体”舔着排队区放着的大冰块时,也应为如此不卫生的举动露出惊讶表情,但当时的我也许因为抱着一种旅者才会有的心情,却能将之简单归类为“文化震撼”。总之,并没有太在意。
印象中当时报章网络也在写,上海世博如何上演各种中国人不文明的戏码,像疯狂盖章就成了世博一大景。那次一个人旅行,我也看到许多人手中握着世博护照,一入馆就略过各种精彩展区,一窝蜂冲向盖章处的奇特景观;只不过让人感受更深刻的是,那时候这一个被笼统概括为“中国人”的群体,其实说着各种方言,操着不同口音,他们来自各地,也和我一样到上海,看一看这浓缩了世界精华的博览会,并且了解他们不太了解的当代中国。
同时,像上海这样慢慢与国际接轨的大都会城市,相信也开始感受到外来人口涌入后造成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在法租界一家西餐厅用餐,坐在旁边一对夫妇由于看不太懂英文菜单,屡遭同是中国人的服务员白眼对待;我很识趣地在点菜的时候说了英语,服务员彬彬有礼回应,但这“差别对待”却让我开心不起来。
因此,自从与中国有直接的接触后,中国对于我来说,就是复杂且多面向的,这个大家眼中的大国,也面对一套独特的挑战与问题。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中国,但中国于我而言从来不仅是一种想象,更准确地说,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场合,让我认识了好多个“不同的中国”。
像曾到北京探望一个在当地念书的新加坡朋友,我们一群人一踏进朋友公寓时,就看到客厅一堆装满的箱子。那原来是我们出发前在淘宝网上购买的服饰物品,当时网购在中国虽未像现在红火,但电子商务和网络营销可能为中国带来的发展契机,已备受讨论。那是中国“智慧零售”的雏形初现。
像到内蒙古希拉穆仁草原上围着蒙古包外营火大声高歌,在库布齐沙漠上与一群同是旅客的洋人打沙漠排球,这些也都原来不在我的中国想象内。最近,我到重庆找同事,我们一起吃晚餐,但不是享用重庆麻辣火锅,而是到他家楼下的日式居酒屋吃烤肉串和喝啤酒;在成都,我的爱彼迎(Airbnb)房东透过微信,和我热烈地聊起杨绛和村上春树等作家,我们在虚拟平台上建立起了某种友谊,这也都是我与“中国”有过的接触。全球化的趋势让世界变得更扁平,随着现代化与开放,中国也在复制着其他城市能供给我们的体验。
当然,也还有身为新加坡华人,对于中国的微妙情意结。
《联合早报》副总编辑兼联合早报网(中国)主编韩咏红上个月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从十九大看中国”讲座上指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中国已开始有意识地输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软实力的领域,中国影视娱乐节目的受欢迎程度也超越港台;中国的文化魅力让一些新加坡人希望新中两国是较为亲密的双边关系,但也因为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感日益增加,部分国人还是认为新加坡与中国应该是“普通的国家关系”,这两种不同的看法,有可能在本地华社与非华社之间构成紧张。
目前,中国的崛起并未从根本上促成本地华文大环境的改善,但至少在学者圈里,区域华人重新汉化,东南亚华人身份可能越来越强烈,是短时间就可能发生的改变。对于新加坡这个多元种族国家来说,即便外交政策论述明晰,中国影响的渗入仍是必须谨慎观察的趋势。
不过,对于新加坡华人能够理性地去认识中国的变化,我还是乐观的。例如,你应该也看到本地歌手向洋和董姿彦如何勇敢地踏出了第一步,在《中国新歌声》等节目绽放光芒。当时,大家都为他们感到骄傲,但不少人并不是一味地倾向中国,只是觉得中国变酷了,而是很切实地思考崛起大国对各领域发展带来的影响。
我们一方面接受中国这个大舞台能给我们这个小国更高的能见度,并且带来经济利益,但同时,国人也心里有数,认识到这游戏有它一定的规则,“能拿下第二名就已经是冠军”的声音就是本地网民对这些选手的“另类肯定”。我猜想,向洋的“红毛派”身份,董姿彦优秀的双语能力,以及他们在台上唱着的西洋爵士,也让新加坡人更容易对他们产生亲切感与认同。
此外,随着中国越来越开放,新加坡人到访中国城市时能感受到的“亲切感”,也很可能是因为所谓的“华人社会”已越来越同质化,或说在价值观与生活习惯上,离西方更近了。对于到当地打拼的年轻新加坡人来说,中国提供的是机会而非诗意;新加坡开埠时期随闽潮移民“下南洋”的南音和潮剧等传统文化,反倒在本地扎根落户后,近年来获得新生命,为新加坡华人的文化自信注入一剂强心针。
如今走在中国城市街道上,我的自在其实不源自于任何抽象的文化认同感。我认为,那更多是因为我通晓双语,能够在必要时迅速转换语码,有时候甚至模仿当地人的腔调,尝试融入。
这份自在也不会影响我在看待中国时的客观。身为新加坡人,我在评价它时少了近乡情怯的感觉,更多的是一种开放的心态。
–伟曼
致伟曼:
在中二开学的第一天,我的华文老师只扫了一眼班级名册,就选了我当华文课代表。
你猜为什么?因为我的名字连名带姓只有两个字,这让我比其他同龄人显得更“中国人”。毕竟,这类名字在中国更常见,有点中国古代诗人杜甫或李白的韵味,不像新加坡华人,更趋向于使用像“Cheryl”这样的洋名或是像“林欣怡”这样的三字姓名。
每次有新结识的人看到我的名字,那个我最怕的问题就来了——“你是中国来的吗?”每每这时,我总会发出最强烈的否认。
我会强调说,没错,我的父母是华校生,但他们在新加坡出生。事实上,他们之所以给我起了这么一个短名字,恰恰是因为一个很新加坡式的原因——希望我能在考试中省点时间。
我今年26岁,但我不像你,伟曼,我是在一种对中国备感尴尬和不适中长大的。我十几岁的时候,从来不认为和中国有联系会是一个为我增加社会资本的事,让我在西化的新加坡同龄人中享有什么优势。
我去世界各地旅行,从摩洛哥到黑山共和国,但就是没去过中国——我外祖父母的家乡。
我妈妈是外婆家三个孩子中唯一生在新加坡的。即便在她大赞中国的发展时,我对中国的印象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虽然在彰显它的新财富,其国人却缺乏社会文明的国家。
我能毫不费劲地用华语和我比较亲近的朋友交谈,而我能感觉到,有些人会看不起像我这样的人。英语被视为都市人想要在职场出头的语言,而华语是邻里的主要用语。
我就这样在自我意识强烈而常感不太自在的少女时期形成了对身份等级的认知,而这让我感觉,拥抱自己作为新加坡华人的根,让我和那些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撇开华人身份的人相比,低人一等。既然如此,又何苦追寻自己和一个很多人都瞧不起的国家的渊源,进一步自取其辱呢?
结果,我越是以自己的种族身份而自豪,我就越觉得中国好像一个影子在变大的幽灵,我必须和它保持距离。
时间来到2010年到2017年,文化的角力慢慢出现了变化。正当我在英国度过大学时光,我的一些朋友,尤其是那些之前在母语课堂上都抗拒讲华语的人,开始去上海或北京实习或学习,而他们对这些经历赞不绝口。
“阿里巴巴”“淘宝”“马云”这些词汇开始出现在新加坡的主流认识中,就连西方媒体都开始关注章子怡、汤唯等中国演员,还有超模刘雯,中国的软实力开始吸引人们的目光。
夸赞中国不再是件很“不酷”的事情了,越来越多人站出来说,中国比生活在新加坡都市的我们更时尚。人力部长林瑞生说,他几年前去上海时,感觉自己是个“山龟”(乡巴佬)。他当时还要拿现金付钱给路边小贩,而其他顾客都用手机上的微信支付轻松搞定。
还有一件事也有类似的效果:英华自主学校毕业的向洋2016年参加《中国新歌声》,这个多年来抗拒母语的大男孩华丽转身,回归自己华人的根。
这个近年来出现的观点转变或许纯属出于功利,譬如是为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可能如你所说,是因为中国的科技发展和现代化。
但在比较个人的层面,它们对我来说是一种催化剂。当主流中的一个群体说,拥抱“华人身份”——不论这是指中国还是说新加坡式的华人身份,这给人一种保证和确定感。
虽然在这场发掘现代中国的复杂层面和细微特质的行动中,我成了迟来者,而且我直到进入大学才开始通过书本和纪录片来了解中国,但我想,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吧。
美籍华人记者张彤和撰写的《工厂女孩——在变迁的中国,从农村走向城市》,还有中国导演范立欣的《归途列车》让我看到在现代中国的洪流中,那些充满鲜明复杂性的生活,还有在这个恢弘的国度,不同人群具有如此不同的面貌。
与此同时,这些也让我对自身的根源更加好奇,也促使我去阅读英培安等新加坡华文作家的英文译本。这些作品以本地视角讲述历史发展,也更贴近我的生活。
有些人可能认为,拥抱华族文化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对新加坡的另一种文化殖民,但我觉得,已经独立53年的新加坡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基因,它让我们难以被任何区域强国所拉拢。
毕竟,有些新加坡华人甚至将中国人视为不同的种族。国家教育学院讲师杨沛东在2013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一些新加坡华人指出对中国人的偏见是一种“种族歧视”。他说,这体现出新一代新加坡华人在看待中国来客时,认为自己和他们是截然不同且有一定距离感的两种人。
如今,我已经不再为自己的名字感到难为情了。“昕”是黎明的意思,或指晨光,而这个只有两个字的名字也让我体会到一种简洁之美。比起每天要被人和这个岛国上成千上万的“Cheryl”或“Andrea”混淆,我会更想要一个独一无二的名字。
或许有一天,当我终于踏上中国的土地,这个名字甚至能带给我一些社会资本。
–袁昕(原文以英文撰写,王舒杨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