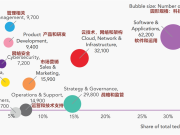《联合早报》和《海峡时报》刊登的最后两封信,主题围绕华人特权(Chinese Privilege)。这个近来经常在网络世界出现的词,在华社群体中鲜少被提及。《海峡时报》记者袁昕在国外生活时曾遭遇歧视,这让她意识到在新加坡,占社会大多数的华人很容易因为存在盲点,无法设身处地了解少数族群面对的问题;《联合早报》记者黄伟曼则回应,华社捍卫母语文化的心,很容易让我们在面对“华人特权”这个严肃的课题时,感到无所适从,但这课题必须获得正视,而探讨这些问题也有助思考华社与华人身份认同的定义。
“特权” 让你正视 它的存在
致伟曼:
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英国冬夜,一群醉汉对我大喊“chink”(对华裔的歧视性用语)。直到那一刻,我才第一次深刻体悟到“华人特权”这个概念。
在新加坡长大的我,日常生活中对自己的种族无所察觉。我从未需要解释自己的样子,或是因为自己的种族而感到被疏远。毕竟,华人在我的国家是多数,而我们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我们的同胞了解我们的文化和传统中的基本价值观和常识。
然而当我来到英国约克念大学,自己身为华人则成了我不太能摆脱的意识。“你到底是哪里来的?”人们会这么问,有时带着好奇,有时则带有居高临下的姿态。
到了晚上,街道变得不太友善,酒精的作用让带种族色彩的语言脱口而出。记得一次暴风雪后,一群孩童将雪球丢向我的新加坡华人朋友。后来我在宿舍看到这名朋友在严寒中强忍泪水。
李笑萍博士(Dr Lee Siew Peng)去年致函《海峡时报》言论版,质疑为什么种族歧视“突然在新加坡成为问题”,掀起轩然大波。本地小说家巴利·考尔·贾斯瓦尔(Balli Kaur Jaswal)对这篇言论十分不满,尤其是李博士说自己一直都自认“就是新加坡人”,直到她去欧洲工作之前都不需要想到自己的华人身份。
贾斯瓦尔指出:“在新加坡,我的印度人身份一直是个问题。当这里的很多少数种族说自己是新加坡人时,都会受到质疑。”
贾斯瓦尔的说法让人想到独立学者和行动主义分子桑吉塔·丹那巴(Sangeetha Thanapal)在创造“华人特权”一词时曾提到新加坡华人的行为,认为和西方“白人特权”如出一辙,也就是无法从非多数群体的角度看待事物。
这些感受让我产生共鸣。虽然我一直都知道新加坡也存在种族歧视,但我只有在出国留学并成为少数群体中的一员之后,才开始用心地“检视自己的特权”。
首先,我开始留意日常生活中和少数群体打交道时的简单言行是否不够敏感,甚至带有侮辱性。毕竟,正是这些生活中的细节形成了我在国外微微感受到的被边缘化。
比如,我的同学会礼貌地赞扬我的英文很好,而不会意识到这正是因为他们的祖辈将我的祖国占为殖民地,造成我们得在学校学英文。也有人在谈话时很容易就说到源自当地电视节目或历史事件的词语,而这些都让我不知所云。
回国后,每当一组人突然有些松懈,开始在非华族同胞面前说起华语,我会尽量把对话带回到英语。
当我的印度教徒朋友在我们聚餐的小贩中心找不到素食选择时,我会转移阵地陪她到附近的印度素食餐馆。我对在决定用餐场所时忘了替她着想感到愧疚。
以前,如果有人对其他种族和国家的人使用冒犯性的语言,我会保持沉默,但如今我会更勇于指出这样做的不妥,因为我知道它给对方造成的痛苦。
本地还是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情况,比如有些雇主在招聘时对少数种族带有歧视,即使工作上并不需要用到华语,有些房东或房屋经纪也拒绝其他种族。
然而,有时“华人特权”也成了一个很笼统的词,显得过于宽泛、涵盖面太大。
教育部长(高等教育及技能)王乙康在2016年国会辩论修改总统选举法令时说,华族社群为了新加坡社会的利益而做出妥协。很多人指出这是“华人特权”意识,纷纷抗议。
王乙康说,华人接受了以英语作为国家的工作语言,同理也会理解保持总统有少数种族代表的需要。
或许他把历史事件和当时备受热议的保留选举混为一谈,是不明智的,因为这是两个不同课题。
上世纪70年代,一代华校生因为学校的主导语言改为英文而经历巨变,并因此感到边缘化。王乙康部长指出这一点,并没有错。
比如,我的母亲中学毕业后就放弃了升学,因为新的英文课本让她学得很痛苦。我知道她因为英语能力有限而在求职中处在劣势,而这也是当时其他原本用马来语或淡米尔语教学的学校学生同样面对的困难。
当一些像李博士那样的新加坡华人能够在完全不受华人身份影响的环境中成长和立足,我母亲的一代人则经历了母语源流学校和南大关闭所带来的巨大冲击。
他们至今仍有些惧怕日益壮大的年轻人群体,包括他们自己的孩子——这些爱讲英语、厌烦华语;不听新谣,而是听美国流行歌曲的新一代。
和其他少数群体一样,他们也担心自己的身份认知可能被一个掌握着过大社会权力的多数群体稀释,而这个群体包括讲英语的华人。
“华人特权”一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框架,探讨作为多数种族会存在的视而不见和无知。
但正如美国作家菲比·马尔茨·波维(Phoebe Maltz Bovy)在她去年出版的“The Perils of ‘Privilege’”(《“特权”的危机》)一书中提到的,“特权”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指控,可能让有关不平等和不公正的讨论沦为一种毫无建设性的个人忏悔和攻击。
如果只是承认自己享有特权,却没有再踏出一步和他人沟通,那就不会改善种族关系。特权也不是一个零和游戏,一个群体自感被边缘化,并不意味着那就可以抵消他们也可能伤害了另一少数群体的情感。
与其互相指责对方享有“特权”,不如让我们带着同理心去理解那些感觉被边缘化的人,无论这是因为种族、阶级或其他身份标志的区隔。
–袁昕(原文以英文撰写,王舒杨译)
“流亡”,我心深处那微妙感觉
致袁昕:
南非反种族隔离的黑人运动领袖比科(Steve Biko)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但因为那不是他的第一语言,他在周围人都说英语的环境里,总能清楚意识到自己处在劣势,甚至在交谈过程中失去信心,感到沮丧。他曾说:“你可能很聪明,但表达能力没那么好……你往往会认为,说英语的那个人在思想上要比你更高一等。”
要突破比科所形容的这种自卑感,我总觉得需要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我在一个讲华语和方言的家庭里长大,即便经后天努力英语已达一定水平,但因说话时表达能力仍欠缺,在讲英语的场合里,至今多少还是会不适应,甚至觉得那已近一种失语的状态。这种“失语”,不表示当下无法与眼前的人沟通,更多因我即使发出声音,却还是自觉有言不达意的地方,是一种心中的感悟。
有时候,在与讲英语的人对话时,即便对方完全不察觉有不妥,并且能百分百理解我所说,我却还是完全可以感受到自己正在做很大的努力,以隐去母语(不管是华语或方言)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我一向来觉得“流亡”是个很重的词,它过于悲壮,但我在和生活于不同语言世界的人交谈时,却往往原地不动就能感觉到自己在流亡,觉得在这个以英语为主流的社会里,自己某种程度上算是个边缘人。
不过,我同时也意识到,这种把自己摆在弱势位置的心态,多么危险。
我同意你所说,在新加坡这个多元种族共存的社会里,我们有时候会忘记自己身为华人,其实是占社会大多数,与少数族群相比,享有一些自然优势,这也让我们在看事情的时候,容易有盲点。
但事实是,在传统华人社群里,华人特权(Chinese Privilege)的概念基本不存在,搜索《联合早报》等华文报章的言论内容,也几乎找不到有人曾在谈论新加坡的语境里,公开使用这个词。在撰写这篇文章前,与报馆较年长的同事提及华人特权的概念,马上能感受到世代之间的差异,一些前辈马上会采防御姿态,基本论调是说:“我们哪里有特权了?”
且不论当年南洋大学和新加坡大学的合并,如何在那一代人心中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如今在华人社群里,即便是少了上一代人的包袱与悲愤的华语源流人士,也多多少少都在教育政策变化中感受过挫折,或至少感慨于社会的逐渐单语化。华社捍卫母语文化的心,因此很容易让我们在面对华人作为大多数被视为享有特权这个严肃的课题时,感到无所适从,尽管两者本应不存在冲突。
然而,过去一年,也许你也观察到,在社交媒体世界里,华人特权却恰恰是我们朋友群中沸沸扬扬讨论的课题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带有明显种族歧视色彩的粗暴言辞,让社会上种族与阶级的分野更明显;在新加坡,启动保留总统选举机制等议题的讨论,一定程度上也凸显了族群差异与种族意识。
去年5月底,本地印族演员巴尔加瓦(Shrey Bhargava)参加梁志强新电影《新兵正传4》试镜,被摄制团队要求以浓厚印度口音模仿典型印度人一事,就瞬间引发网民热议。我的面簿朋友群中,好些马来与印族朋友诚实地分享了看法,也描述自己与华族同胞相处时,曾被不经意言论伤害的经历。
同时,我也看到一些华族网民对此事发表不敏感言论时仍能理直气壮。这促使我不得不开始思考与正视种族歧视的问题,并且检视自己的言谈举止,是否也曾逾越界限。
2016年,南中国海仲裁案课题和新加坡装甲车在香港被扣留的事件,曾让新中两国关系进入低潮期,网上部分舆论当时倾向新加坡应在外交战略上与中国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多少也触碰到少数族群的敏感神经。本地剧作家和诗人亚菲言(Alfian Sa’at)就此分析说,本地华人族群中这种情绪的涌现,或多或少象征着“某种被压抑的文化与政治身份的卷土重来”,与过去华社部分群体曾感觉被边缘化有关。他指出,华社应有所警惕,不应为维护这份“过去被压抑的尊严”而让主观情绪影响判断。
当然,亚菲言的言论不一定具代表性,甚至一些人可能会觉得当中存在对华社的误解,并且质疑“华人特权”这严厉的指控是否有足够的现实依据,或是这词其实在互联网更开放的舆论空间里,已被滥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华社必须正视他抛出的问题:一个崛起的中国会不会动摇本地的社会凝聚力和国家主体意识?
另外,这也进一步揭露另一更宏观的问题:本地华人应该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认同?传统华社的定义是否应该放宽?
我认为,新加坡政策研究所去年5月至7月间展开的一项国人族群身份认同调查结果,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本地华社面对的挑战。尽管华文华语式微,大多数人仍将族群认同感建立在语文的掌握上,而与此同时,本地华人对祖籍观念和华族传统与传统艺术的重视则相对变得薄弱了。
在与报馆其他同事了解他们对华社的看法时,有不少人就指出,广泛定义的“中华文化”已无法让年轻人有归属感。也有同事反问:“对于一个定义模糊不清的东西,我要如何产生认同感?新加坡华社的定义是否能扩大到跨越语言和肤色,代表着一群热爱华族文化的人?”
值得庆幸的是,这一连串的问题和反思,很可能也代表本地年轻人在看待认同问题时,视角已变得更包容,甚至有了更丰富的历史和世界观。新加坡明年纪念开埠200年,趁着思考这个历史命题的同时,我们是否也能以更开阔的胸怀拥抱我们身为华族、新加坡人,甚至是东南亚人的身份,并接受这其中的复杂与多元?
谈到认同问题,我总会不禁想起大学时期,曾为探索身份认同问题,访问著名学者王赓武教授的情景。当时,教授从他1950年出版的英文诗集“Pulse”(《脉搏》)中挑了一首题为“Ahmad”(《阿末》)的“马来亚诗”,深情朗诵,为我们述说他对这片土地的原始情怀,令我印象深刻。不知怎么的,尽管我对那从未认识的“马来亚”只能有想象,但教授办公室回荡着的声音竟触动了我心深处某一块东西。那微妙的感觉我至今无法解释,但也觉得没有必要刻意去定义或为它寻找什么坐标。
–伟曼